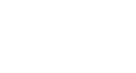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原文载于共识网。
英国公投、美国特朗普主义、中东乱局、恐怖主义持续、欧洲难民潮和极端政治力量勃兴、拉美民粹主义从左派转向右派、亚洲地缘政治之争等等,都指向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秩序出现了大问题。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人们都面临着秩序和治理问题。内部秩序和治理危机是政治权威衰落的结果。诚如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秩序由权威所确立,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政治权威衰落了,秩序就不可避免发生危机。再者,当前的国际秩序危机和内部危机是互为一体的。内部危机可以外延成为世界危机,例如中东政权的解体所造成的欧洲难民潮。另一方面,外部力量也可以构成内部治理危机。中东政权的解体大都是外部干预造成的。英国公投也是对欧盟的不良发展的反应。
秩序和治理危机如何发生?所谓的秩序就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危机是过去三大转型的产物。这是从二战之后开始发生,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到今天仍然继续。
第一大转型是从国民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近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化一直在发生,但并没有形成像今天那样的全球经济。国民经济指的是各国享有经济主权。在漫长的国民经济阶段,各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贸易和投资。尽管从对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对国内各个社会群体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有能力通过税收等机制来调节,补偿受益不多和甚至成为受害者的社会阶层。
当世界进入全球经济时代后,所有国家对全球资本都失去了有效主权,甚至完全没有主权。除了少数像朝鲜那样的封闭经济体,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权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质,脱离了政治和社会的制约,即使遇到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阻力,也能够自行全球化。通过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利益仅流向资本及关联的少数社会成员,形成了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当资本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政府则陷入困境。各国的税基大大减小,政府缺少收入,很难再通过传统的收入分配方式来保障社会公平。富豪经济已经使得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加大,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则失去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全球经济已经重创今天的中产阶层。从就业就可以看出今天中产阶层的恶劣环境。在西方,中产阶层由从前的产业工人转化而来。但全球经济产生了两个要素,改变了就业局面。第一,技术的流动。在国民经济时代,技术产生就业,一个技术的产生往往导致一个产业的产生,从而也是产业技术工人的产生(就业)。但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往往把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技术的产生,既产生不了产业,更产生不了就业。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区。第二,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导致了劳动力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这种流动有“非法的”,例如涌向欧洲的难民,也有合法的,例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有其理性,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对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技术进步则更是对就业产生致命伤。技术产生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技术不仅不产生就业,而且减少就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这样。6月25日的《经济学人》专门讨论人工智能问题。一项研究认为,在今后的10至20年里,美国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作岗位要被自动化所取代;而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百分之十。
资本逃避本国制约
第二大转型是从精英民主转向大众民主。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精英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今天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在精英民主阶段的早期,政府仅是资本的“代理人”(马克思语)。发展到后期,政府则通过保守的社会政策,通过保护社会来保护资本顺利运作。在精英民主阶段,资本利益和政治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是合一的。但进入大众民主阶段之后,政治利益和资本利益开始分化。从前是资本和政治的结合,现在则是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
这一转型的积极结果,就是社会政策从早期的社会保护转型为全面的福利社会。尽管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大众民主没有多大关联,但大众民主有效地推进和扩展了社会政策。在福利社会,民主和福利几乎是一体的,民主选举往往成为政治人物之间的“福利拍卖会”。被视为是理性的选民,在投票时不需要做多少理性思考,只看哪一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社会政策对资本运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政策表示对资本的制约和规制,不仅表现在高税收上,也表现在诸如环保、安全等方面。面临种种制约和规制,资本开始逃避本国社会。资本逃避本国也构成了上面所讨论的全球化的动力。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资本驱动的。这种动力机制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第三大转型是知识方面的,即从世界化转到地方化,从宏观转到微观。近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在社会转型方向和转型方式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新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构建。离开知识和思想,就很难理解近代以来的进步。但是,今天的知识界的性质已经今非昔比了。知识完全受政治和资本两种力量的影响,甚至支配,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并非出自社会大众的需要,而是政治和资本的需要,政治和资本决定了研究者能够研究什么和不能研究什么。
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大众民主时代,诚如美国已故众议院院长欧尼尔(O’Neil)所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在精英时代,政治精英具有全球眼光,在决策时往往能够把国际环境考量在内。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所有政治都地方化了。这对知识界也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例如,数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对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反思少之又少,大多数完全失去反思的精神和勇气,仅扮演论证民主和推广民主的政治工具。与民主研究相关的发展,就是学术界把认同政治研究推向了极端。
认同政治走向极端
知识的这种转型自然也影响到实际政治。今天,从西方到非西方,认同政治达到了顶峰。认同政治强化了人们的地方感,而失去了大局感,演变成极端的民粹政治。凡是地方的,所有的小事都是大事;凡是国际社会的,所有大事都是小事,与己无关。在认同政治下,政治空间被政党所分割,社会空间被市民社会所分割,大家只有激进的个体感,而没有社会整体感。政党、环保团体、动物爱好(保护)团体等团体活动高度政治化和急进化。
前段时间台湾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尽管在台湾之外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但很能说明政治地方化的现象。台湾陆战队员杀害了一条流浪狗,引发动物保护团体包围了国防部,部长出面道歉献花,海军司令被抗议人士丢花束,三名翻案士兵与直属上校长官向动保人士行礼致歉的画面,还被放上面簿直播。之后台湾海军共惩处九人,三名犯案军人有两人记大过,列入汰除对象并移送法办,督导不周的长官共六人被记过。让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地方化的事件(动物权利认同)竟然能够引起台湾那么多的关切,而与台湾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大问题,例如台湾的民主、福利社会等等,则很难有同样的关注。
从一定程度上说,一些形式的恐怖主义也和认同政治有关。一些年轻人通过认同某一理念(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自我激进化,加入恐怖主义队伍。西方社会那些自我激进化的年轻人,就是在拒绝认同西方价值的同时,选择了自己的认同。
资本对学术研究转型的影响甚至比政治更大。资本控制学术研究经费。各种研究基金表面上具有开放性,但实际上紧紧控制了研究人员的研究意向。凡是符合资本利益的课题,有大把的钱;而不利于资本的课题,则被封杀。资本通过为研究者设计“激励机制”的方法,悄悄地改变了研究者的研究意向。同时,资本也帮助政治人物来控制学术研究,例如今天大学对教授和教师的考核,和资本对劳工的考核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很多大学,本身就已经变成一个资本组织,学术研究和资本领域统一化。
在政治和资本设计的知识笼子里,教授和研究者失去了思考大问题的能力,不去提重要的问题,而只能在微观层面就事论事。他们不去问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数十年来,尽管社会科学被认为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产生一位像18、19、20世纪初那样的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例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教授和研究者大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技术工匠”,他们不问是非、不问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做研究的目的。结果就是政治和资本很容易确立了“意识形态的霸权”。
今天,这三大转型仍然持续,并且有加速的势头。除非减速甚至扭转这三大转型方向,否则人们不得不继续面临日益恶化的秩序危机。人们要不回到前霍布斯时代,要不进行大变革来重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