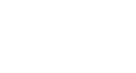近日,我院博士后、经济学博士王璐瑶在澎湃新闻发表文章论述特朗普时代的中美BIT谈判问题,原文如下:
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2017年2月27日。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任前曾放言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高关税,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让外界对可能爆发的中美贸易战的关注度急剧升温。那么,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又将何去何从?
特朗普上任伊始即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重谈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称将通过双边谈判的形式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并服务于“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典型的美国保守派的价值主张。相较于奥巴马方面的实质性战略转向,特朗普将经济协定谈判的重心从多边转移至双边,在给双边谈判带来更多动力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多期待和压力。
截止目前,中美两国已在2016年底于华盛顿完成第31轮磋商,并交换第3次负面清单改进出价,形势焦灼。美方不仅在代表市场开放度的负面清单领域颇有怨言,其国内还有声音认为,在BIT谈判过程中,美国不应再将如今实力强大的中国继续作为发展中国家看待而过多妥协,反而需要借助BIT谈判,促进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并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同时推进“竞争中立”规则,以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凭借国家补贴和政策扶持而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的优势。
与此同时,美方也十分看重对规则主导权的维护。正如特朗普方面并非完全反对国际贸易而是寄望于重新建立所谓符合美国利益的公平贸易规则,美方在国际投资领域的逻辑也是如此。国际制度是国家权力的附属现象,因而美国此前力推2012 BIT谈判模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旨在维护自身提供治理规则作为公共品的既有垄断优势,进而通过主导议题设置和标准构建,来为中国增设门槛。这尤其表现在中美BIT谈判中美方极力强调“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等美式规则方面。
理论上,外资流入(FDI)可能带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符合特朗普任上目标。外资流入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包括“直接效应”,即FDI企业通过新建项目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及主要与FDI企业贸易活动有关的“间接效应”,例如进口活动可能使部分本土企业产品被替代,从而导致市场需求减少而企业裁员,出口活动则可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使得业内企业增加雇员。
近年来中企对美投资持续增长,潜力巨大。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实现历史突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位,并首次超过同期外资流入水平从而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同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亦再创新高,同比增长5.7%至80.3亿美元,且境外企业雇佣美国当地员工8万多人。特朗普所看重的制造业以40.1亿美元高居榜首,同比增长122.2%,占2015年中企对美投资全部流量的49.9%。此外,美国还是中企对外并购的第一大目标国,仅2015年中国企业对美实施并购案就达到97个,上海复星国际、安邦保险、万达集团、海航集团等发起的并购项目均在其中。
但是,中国对美投资相对规模仍然有限且易受东道国政策影响。从占比看,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仅占中国全部对外投资的5.5%和3.7%,与两国经济地位甚不匹配。并且,中国企业屡屡遭遇来自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困扰。美国对外资的审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依据美国规制外资跨国并购、保护国家 安全的基本法《埃克森-弗罗里奥法案》(1988年)进行审查;二是美国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分别依据“国家工业安全项目”与“关键行业”条款对外资进行审查;三是成立美国战略物资保护委员会以约束其他类型的投资交易,该机构至少每两年一次,就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物资进行评估并向国会报告。
在美国三位一体的外资审查体系中,CFIUS属于跨部委机构,其审查范围通常包括评估相关投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国防工业、相关科技与资源、通讯与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国土安全等。其中,“外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美国的某一公司或产业”这一审查情形通常被视为特别针对外国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发起的对美并购案。CFIUS最新报告显示,2012-2014年,CFIUS就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展开的并购审查案达到68项,约占同期CFIUS对全球企业对美投资发起的审查案的五分之一。33项位于制造业,其余主要位于采矿、建筑、金融、信息等行业。仅2014年中国企业遭遇的CFIUS审查案就高达24起,位列国别排行榜首位。这与中国对美投资的较小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从历史趋势看,美方还会继续坚持以“国家安全”为审查为核心的外资监管体系。通过对美国历任行政当局的外资政策梳理,可以看到,美国经历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投资自由化”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特方面的“中立立场”,再到里根方面以来开放市场与外资监管并重的转变历程。
美国外资监管框架的建立与完善是个案推动与外部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外资审查的核心条款《埃克森-弗罗里奥法案》及此后对其加以拓展完善而形成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007年)与美国先后经历的日本投资潮和新兴经济体投资潮密切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利益相关体的外资流入展开更为严格的监管。如今,延续外资监管势头并重视外资的社会经济效益,也同样符合特朗普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如此看来,特朗普方面对待中美BIT谈判的心态应当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中美BIT谈判是两国就双边投资问题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也是大幅推进双边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市场,进而在中国对外投资急速增长期内分享更多成果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特朗普方面也会对缔结一项能够显著增强中国投资权力的协定心存顾虑,因而可能会更加强调平等互惠和对等开放,在推进负面清单和涉及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规则时更为强势。
然而,特朗普方面也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和中国的选择。美国自里根执政以来,除克林顿外的国家首脑均在任期内发布了积极友好的外资政策声明,在加强外资监管的同时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即使是没有发表外资政策声明的克林顿方面,其在任期内联合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试图建立的外资监管框架也包含了消除资本自由流通的障碍性因素等促进外资流动的措施。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过度坚持及保护主义策略,在强化外界对新一届美国行政当局立场和底线认知的同时,也会使得美国陷入被动处境。
作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双边制度安排,中美BIT谈判无疑有着强烈的信号释放作用。换句话说,无条件的“美国优先”不仅会影响中美BIT的谈判进度,还会影响其他国家是否以及如何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战略选择。特朗普上任前后以及最终宣布退出TPP时各国的反应可对此进行印证。迄今为止,众多国家开始转向中国以寻求与亚太市场更加深入的联结。加拿大等国家开启与中国的双边经贸谈判之旅,其他数个TPP成员国表态愿意考虑加入或加速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以期早日达成协定。
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如今在国际经济协定谈判中存在更多选项,自然在中美BIT谈判中也拥有更多底气。
从时间轴看,中国经济权力的对外塑造,正在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转变,从早期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国内发展,到如今强调公共品供给能力和包容性发展转变,因而在协定谈判和规则构建方面也会更加主动。一方面是在接轨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国际新规则方面显示谈判诚意,如在中美BIT谈判中承诺引入负面清单模式,并在多个地方省市设置试验区,进行改革探索;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推出规则和设定标准,这从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发布全球首个投资指导原则可见一斑。具体到中美BIT谈判,中国应将此作为重新定义中美在投资领域利益和共识的契机,并借此明确中国在双边和国际投资领域的利益诉求和治理路径。
从空间轴看,中国正在迅速推进自贸区(FTA)战略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力求最终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FTA网络。新一代的FTA谈判通常涉及投资规则,谈判重点也逐渐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转移,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内措施”转移,并涉及竞争和供应链等新型议题。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美BIT是中美FTA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完善全球FTA战略的重要环节。从策略上看,中国同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协定谈判,如中欧BIT和中加FTA谈判等,都将产生一定的“竞争性自由化”效应,有利于中美BIT谈判推进。
原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7925